我和我的三亚·这方水土这方人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去过几次崖州,突然悟到三亚的“乡愁”应该具象到乡村,山水之间,气象万千;民族风情,天宽地阔。
这方水土这方人。自汉武帝开郡,三亚一直是州郡县治所,经过两千余载发展变化,积淀下丰厚的历史文化。如此背景下的人们,生生不息,根植沃土,创造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雪辱霜欺梅花依旧向阳开。三亚和三亚人,古朴有风貌,当代有追索,未来尤可期。
这大概是一家本土媒体和一名媒体人特有的使命,因为我们都深深爱着这里,爱着这片土地——三亚。
临高村│寻找郑绍材
■临高村
位于崖州区中心偏西,宁远河西北岸边,是保港片区进出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郑绍材
郑绍材(1876年-1921年),字华千,号贞山,乡谥文正,崖州五都临高村人。其幼而孝友,聪敏过人,尝从孙发南先生游。弱冠以州试第一、府试第二进庠。光绪庚子辛丑(1901年)恩并科举于乡,成为崖州最后一位科举制举人。
民国元年(1912年),任崖县议会议长;民国七年(1918年)6月28日,被地方各界推举为崖县代理知事。
从临高村铺仔市路口走进十几米,“崖州最后一位举人”、曾全力筹钱重修《崖州志》的郑绍材的故居,被3片一人多高的铁皮围挡着,要站在“邻居”的台阶上,才能瞥见一二。

崖州区临高村铺仔市路口的骑楼群,最左侧有围挡的即为郑绍材故居。 记者 王鑫 摄
那3片深绿色的铁皮连在一起,像一排弧形的树,静默地矗立在初冬的阳光里。
两个多月前的9月19日,崖州区保港和美渔村一期——临高村古建筑保护修缮项目暨全国工商联“万企兴万村”实践点开工典礼举行,此次古建筑保护修缮项目(一期),选取的就是以重点保护性历史建筑郑绍材故居为代表的3栋历史建筑。
“铺仔”的大意是“小卖店”,郑绍材故居也曾是当年的老字号商铺——嘉祥铺。这里面,有过繁华与落寞,更有他后代所说的“无尽遗憾”。
身为骑楼建筑,它又似站在那里的瞭望者,一眼过去,一眼现在。
举人之举
从郑绍材故居拐进一条小巷走几百米,是他的孙子郑辉史的家。
在一段院墙下,74岁的郑辉史轻轻抚摸着叠在一起的两块长条花岗岩说:这是爷爷当年中举时,“衙门”给的。
石头上的字迹已经很难辨认,郑辉史“翻译”说,“爷爷当年中举的成绩是崖州第一名、海南第二名、广东第一百二十名。”
关于郑绍材中举后的“为官之路”,是史是说,“风评”皆佳。
据史料记载,其在光绪庚子辛丑(1901年)恩并科举于乡,后被选为崖州、万宁、陵水、昌化、感恩五属谘议局议员。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郑绍材赴京楝选得州判,民国初年历任崖县会议长、团练局长。
1916年与1918年,因政局不稳,各役县官挟印潜逃,临事无主,郑绍材在极其艰难的时势下,先后两次权理县篆。
郑绍材是一位有担当的官员,在主理崖州事务期间,革积弊、除陋规、复学款、置仓田、刊州志、修族谱等,得到州人的称赞。
郑绍材于1921年去世。郑辉史说,爷爷离开的最大原因是“操劳过度”,“那年他才45岁,多么年轻啊!”
郑辉史介绍,爷爷原本葬在崖州大疍村乌石山坡,后迁至现在的宝平山安置陵园,保存了原来的墓葬样式。
郑绍材的墓碑正中写着:前崖县知事清举人举孝廉方正乡谥文正郑太公之墓。墓碑周围是镌刻的墓志铭,其中民国时任广东公立法政学院院长区大原写的铭文引人注目——
“君于议会中,固不肯为庸庸者”“凡一切地方公益,见义勇为,如革积弊、除陋规、复学款、置仓田、刊州志、修族谱等”“然而世事沧桑,频年变乱,离群之感,时实为之。虽平昔之执友之交,往往有涯角暌违,杳知隔世者,而何独于同年,郑君为然也哉”“珠之产崖也,为南海之精。君之生于崖也,为多士之英。遭时变乱而尽瘁乃事也,义务为重,权利为轻。藏之永固,垂不朽于来兹也,将与金石而同贞”。
对于郑绍材功绩的评价,可见一斑。
区大原在墓志铭中也提到了郑绍材家风的一面:君生平笃内行,菽水承颜非循故事,只事继母,深得欢心。抚诸弟妹一如所生,此事虽至近且庸者,实难能而可贵。
郑辉史说,在崖州大疍村南面安置着其曾祖父、曾祖母的合葬墓,墓碑上刻有“皇清例封文林郎 正孺人 授 奉直大夫 五品宜人 附贡生郑二老太公婆之坟”。郑绍材在墓前修建了两根华表柱,刻有“光绪二十七年卒丑补行庚子 恩正并科举人郑绍材立”字样,其心之孝、其情之真,令晚辈们感动。
不吝重修《崖州志》
现存的《崖州志》版本中,民国三年(1914年)的版本分量尤重。
郑绍材撰写了《新刊崖州志跋》:钟牧元棣重修《州志》,书成于光绪辛丑,补订于戊申间。筹出版而未果者,不止一二次。甲寅春,偶与孟君继渊谈及此事,幸具同心。继而商诸大众,胥有厥志。但因的款未敷,而欲暂待。绍材特于先君名下加捐八十金以足之,亲携缮本,赴省排版。版初出,其误点悉为校正,凡三匝月而工竣。印成一百套,分饷州人,非敢谓克竟前后修辑者之志也。窃喜此书印刷既观厥成,流传自当永久。而后生考古,不致兴文献不足之嗟,是则区区之心耳,以谂来者。
这些文字,是郑绍材去广州印刷光绪《崖州志》期间,于旅寓写就。此事由他和孟继渊等助力促成,其父亲也承担了一部分费用,可以说为保存崖州重要的史料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崖州志》一再续修并重见天日,民间捐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事的源头是辛亥恩科举人吉大文、崖州知州唐镜沅提出修志,终以“赀巨难筹,事仍中止”,因为资金不够而搁浅,后于庚子年(1900年)5月开局纂修,得于知州钟元棣自捐廉百金,州官带头把工资捐了出来,乡绅深受鼓舞“皆乐捐赀以赞其成”。在此背景下,郑绍材等人再次筹措资金,印刷成书。
2017年《海南日报》曾有报道,海南民间文艺工作者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发现7册残本《崖州志》以及捐助者芳名录,佐证了上述记载。
在发现的《崖州志》“捐输名单”里,有详细资额,多则四百、一百,少则二元、千文,既有文武官员、阖州士民,也有阖州公会。
其中,知州钟元棣倡捐银四百大元、协镇朱心源捐银十大元、学正梁宗榘捐银十大元,恩贡玉墀、岁贡赵以濂、附贡郑启书各捐银一百大元,州同麦廷琛、尹如鹏、王嘉珍各捐银五十大元,举人郑绍材捐银二十大元,廪贡孙毓斌(崖县第一任民选县长)一十五大元等。
另外,捐五元的有20名,四元的7名,三元的8名,二元的5名,有功名者较无功名者捐输为多,州知、州同、县丞、守备、理问、经历、千总、把总、举人、贡生、监生、武生、生员、商民、普通民众等共91名合捐银一千七百零伍元另加一百三十一千一百文。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二十六年,知州钟元棣欲续修《崖州志》时前志书泯灭,幸得何秉礼家献出家藏手抄孤本方得重修。此事被钟元棣记录在《重修<崖州志>序》中:访问州志,则何绅秉礼家尚有手校本。
被《崖州志》列入“笃行”一章的何秉礼,字竹筠,崖州起晨坊人,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选登癸酉科拔贡。
郑氏后人“地震学家”
郑辉史说,临高村的郑氏家族里,叔父郑联达成就最高, 曾为兵器工业部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从2010年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说起,称叔父曾用自己发明的“冷起辉式日光灯”对地震进行过科学探测,并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身心投入研究撰写了《大地震规律研究》《唐山地震研究》等专著,其提出的预警地震概念被学术界推认为“地震预测新概念”,被认为是中国地震科学最为前沿的代表人物之一。
郑辉史说,叔父1932年在崖州读完初中后,赴广州读高中,那年他才16岁。1937年,郑联达考入广西大学物理系。1939年郑联达到达昆明,转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就读,1942年毕业,一直致力于物理教学工作。唐山大地震之后即转入地震预测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有人称郑联达“大器晚成”,或缘于此——他的地震科研是从60岁开始的。其在夫人王懿云2002年过世后,把自己“关”在住所里搞科研。到90岁高龄时,仍坚持每天盯着灯光的变化做记录找规律,争分夺秒。
2010年7月出版的《北京理工大学校报》刊发郑联达的得力助手周化南的文章:《怀念郑联达先生》,回忆了郑老先生的一些往事。
1974年,郑联达偶然看到日光灯在关闭的情况下自动启辉,对这一现象十分好奇,想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于是买了很多日光灯管和变压器开始做实验,从此开始了在地震这个全新领域的研究。
郑联达逐渐发现,地电变化和灯自动亮有关系。而地电变化是地震之前的一个预兆,即日光灯自动亮是地震的一个预报。他每天都要多次定时用手调变压器调到灯亮,记录下这个时间的电压数,几十年如一日。
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浩劫———是郑联达心中永远的痛,“地震对人类的伤害太震撼人心了。”这也坚定了他坚持从事地震研究的决心,“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希望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减少地震带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和生命损失,这样自己走了也安心。”
郑联达在《记一场奇怪的比赛》的文章中写到:“我是个近古稀的人,经常想起两个问题:一是一生中有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安慰的事,一是在所剩无几的岁月中如何度过?对于有着英雄业绩或者文笔才华的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是够他写的了,但像我这样教了一辈子普通物理的人能写出什么来呢?”
就是这样一位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疯老头”,就是这样一种不放弃不服输的精神,为中国的地震研究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于80岁时出版两部关于地震学的专著。
斯人已逝。郑辉史常常看着摆放在桌子上的爷爷的照片陷入沉思,那些黑白的画面闪烁着动人的色彩,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里——
自有人随风,自有人入梦,自有人长留心中。
郑辉史│爷爷那一大箱子书,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87岁的郑联杰,是郑绍材的堂侄,也住在崖州区临高村。
11月28日上午,他来到堂侄郑辉史家中,说了几句话便匆匆离开。
刚从三亚市区回到临高村的郑辉史10岁孙子,一边摆弄着爷爷的手机,一边听爷爷讲着爷爷的爷爷的故事。

郑辉史祖孙俩找出郑绍材当年文章的“木刻版”,仔细辨认。
故事里的“郑氏人物”,都重学习、有毅力。在郑辉史心中,上至地震学家叔父郑联达,下到在海口工作的兄妹,当然也包括一路拼搏过来的自己,皆有良好的家风传承。
郑辉史能记起父辈讲过关于爷爷的往事——
郑绍材家里养的牛在山上被人偷了,窃贼很快被抓到。他回到家中得知情况后,吩咐把人放了,再送一点钱财,说这个人肯定遇到难处才会这样做。“爷爷还跟那个人讲,再苦再难也不要当贼,干这个怎么能真正发财呢?”
有一次,郑绍材“下班”途中被拦劫,随从将人抓到。经询问,那个人“喝多了”,之后郑绍材也没有追究任何责任,跟对方说不要再喝酒了,会误事。
“爷爷的口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郑辉史说,叔父郑联达讲过“父亲是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人”。

郑绍材文章的“木刻版”,落款处他的名字清晰可辨。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王集门、罗灯光、黎月光编著的《崖州古文百篇》里,收录了一则郑绍材撰写的《空车救回樵人事述》,记述的是他的曾祖父费时费力,为救砍柴樵夫空车来回的事迹:
“昔我曾祖时清公,尝驾车斫柴,鸡鸣而往,同行者六七人。黎明将及山,道左先有牛车在焉,其人身卧车中,牛行渐迟,至阻后车之过。呼之不应,共视之,则其人毛发为车轴卷,气垂绝矣……既而众敦促去曰:是已死矣,虽救之,于事何济,徒误我时间耳。公曰:人命关天,虽今日空车而归,吾必不能弃此也”……
随后,郑绍材的曾祖父“独吸其鼻口尽血,数十吸而其人苏焉”,并用车将其拉回家。出去一天没有砍到柴、空车而归,但他舍利救人的善举令人难忘,“数传后,其子孙犹纪念不忘,时相往来,其邻里至今称道弗衰”。
郑辉史的父亲并没有承继为官为宦的衣钵,但与“重视读书”的家风一脉相承,从当时的广东国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回到崖州做起小买卖,开了“百货商店”。1938年,他带着家人到了乐东,后又返回崖州开药铺。
郑辉史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长大后种地、卖槟榔,干过很多工种,1999年靠积蓄盖起的两层小楼,如今依然坚固。
“我们郑家几代人,就是一部奋斗史。”郑辉史说,他们都知道靠自己才能安家立命的人生道理,所以“从不给别人添麻烦”。“我自己家最困难的时候,是5个孩子都要读书,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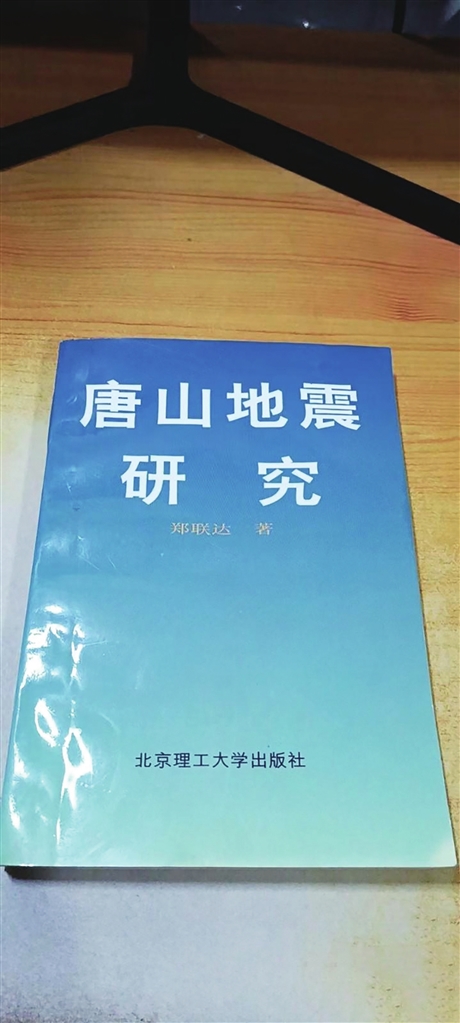
郑绍材儿子郑联达所著《唐山地震研究》。
自1932年出岛后,郑联达只回来过两次,一次是1946年,一次是1988年。这中间,郑辉史曾到北京探望叔父,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房间里都是书”。“也有人问他,说三哥你都退休了,工资也够用,这么辛苦干啥?他反问人家,‘你说什么是辛苦?我要把所学的、所懂的奉献给社会,这才是我最大的幸福’。”
最后那次返乡的时候,郑联达一一拜访曾经资助过自己读书的人,“他还了大家的借款,还有利息。”
对于先祖们的情况,郑辉史的孩子能说出每一个人的名字。“这孩子比我们大人聪明。”郑辉史还讲了一件小事,“那年家里的孩子要去广州读书,装东西的密码箱突然锁住,一屋子大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我孙子显得‘非常冷静’,他上网查询了一下,三下五除二就把箱子打开了。”
郑辉史的家里,至今保存着郑绍材当年考举时写的3篇文章之一的“木刻版”。郑辉史说,这样的刻版本来有3块,他们从老宅子搬出来后都遗落在那里。后来,还是有心人看到1块后归还给他。
“我记得还有一大箱子书,都是爷爷留下的,后来才懂得它们的珍贵,但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郑辉史抚摸着那块“木刻版”,上面鼓起的字刻依然坚硬,它们一个一个顶在郑辉史的手指上,甚至让他有隐隐的刺痛感。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王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