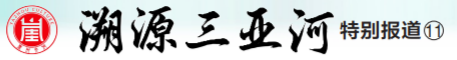

三亚河滋养琼崖大地。图为白鹭在浅滩上觅食。记者 陈聪聪 摄

穿城而过的三亚河。记者 陈聪聪 摄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是朝廷平定南越国后第二年,朝廷在岭南设置九郡,汉武帝在海南岛上设置珠崖、儋耳二郡,共辖十六县。海南从此告别荒蛮无主的状态,正式接受汉朝的层级行政管理。
很多人想当然将当时的三亚地界归入珠崖郡,其实《正德琼台志》说得很明确,崖州境为“儋耳郡地”。二郡设立29年后,儋耳被裁撤,琼南才隶属珠崖郡。35年后,珠崖郡亦被裁撤,海南岛被遗弃89年。此后的漫长时间,海南岛上没有郡级行政机构……那么,三亚河流域的早期行政隶属是怎样的?山南、临振、临川、落屯,一个个带着远古余温的名字,与三亚河又有怎样的关联?
山南县,是否覆盖了三亚河流域?
西汉《茂陵书》记载珠崖郡和儋耳郡下辖共五县:玳瑁、紫贝、苟中、至来、九龙。《正德琼台志》综合《汉书》记载提出异议:“又曰山南县反,又曰合十六县,又曰九县反,则县不止五”。或许,在元封“五县”后陆续有增置,是否真有“十六县”已无史料佐证。
文中“山南县”让我们感觉到历史的温度,三亚河流域位于群山之南。百度搜索的资料,将山南县治锁定在陵水县椰林镇里村,但没有任何史料和考古资料支撑这一说法。陵水县南北均有大山延伸入海,进出受阻,当时人烟稀少,达不到置县条件;里村位于陵水河口,当时也未必成陆,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设置的陵水县尚且西属临振郡,而非北属珠崖郡,牛岭以北至万泉河之间的广阔地带直到唐朝才开始设置行政机构。元封“五县”最南面的九龙县,位于东方市感恩河口,其南部仍旧是一马平川,拥有更多空间可设置行政县,不可能越过众多河流和山岭绕弯至陵水置县。明万历《广东通志》认定山南县就是当时的崖州地界,即三亚市和乐东县境。《崖州志》推测西汉“十六县”中有乐罗县存在,位于望楼河下游,那么山南县治只能在更南方的河口,可以锁定在三亚市境,要么在宁远河口,要么在三亚河口;藤桥河口远而多山阻隔,基本可以排除。三亚河流域位于中部山地正南,在西汉更有可能设置山南县;即使位于宁远河口,三亚河流域亦可归入山南县地界。
“山南县反”在西汉史书上记下一笔,是当时海南唯一被指名道姓的县级“负面新闻”,说明这地方民风彪悍,百姓不堪官吏压榨而奋起抗争。从地理上说,山南县属于琼南极地,天高皇帝远,人们更崇尚自由,受不了王朝礼法约束。当然,《崖州志》也对山南县的存在提出疑问,因为其出处《汉书·贾捐之传》一文并无此文字,或摘于其他古籍。不管怎么说,三亚地界自打设置行政机构,就在中原王朝统治者心里打下了浓厚的边地烙印。
冼夫人的“汤沐邑”,临振县在哪里?
时间来到南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535年—546年),崖州设立,结束了海南275年州郡级行政机构缺失的历史。这一设置,得益于岭南新兴的冯冼家族,其核心人物竟是一介女流,她就是冼夫人!
她是一个俚人部落首领的女儿,有说名冼英,有说名冼珍,嫁给罗州知州冯融之子冯宝后,她就成了冼夫人。当时,俚人遍布岭南之南,包括广东、广西的南部和整个海南岛。冯冼联姻就是汉俚两大民族的结合,促进了岭南民族大融合,农耕民开始大量登岛,海南俚人与两广俚人联系渐少,独自发展成了当今的黎族。总之,冯冼家族成了岭南第一家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200余年。设置崖州,就有冼夫人的意见,他们为梁朝平定了岭南叛乱,并且慧眼识英雄,资助交州刺史陈霸先北上,最终建立陈朝,加深了冯冼家族与朝廷的“蜜月”情。
冯宝英年早逝,冼夫人成为家族核心人物,继续忠于朝廷。到隋文帝剿灭陈国,她率领家族对陈国做了最后的悼唁,归顺大隋,使广袤的岭南大地得以“和平解放”。此后,她仍旧运筹帷幄,指挥部下平定了数次叛乱,光环达到鼎盛,最终受封谯国夫人,赐“临振县”为其“汤沐邑”,享用1500户赋税。
那么,临振县在哪里?
在天涯区文门村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冼夫人受封汤沐邑,派家臣虎豹将军来到文门村,与临振县各俚人峒首歃血为盟,约定忠于朝廷;县治就位于至今都是黎族聚居区的文门村,这就是冼夫人的汤沐邑……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文门村地属龙海盆地,肖旗水在此发源并流向天涯湾;肖旗水的分支大兵沟与汤他水同源,这一带亦属三亚河流域。那么,临振县是否就位于三亚河流域?
有人将临振县归为西汉“十六县”之一,若真如此,西汉时期三亚境内就拥有山南、临振两个县,三亚河流域总会摊上一个。《嘉庆重修一统志》之《崖州》则记载:“隋开皇初,置临振县;大业六年,置临振郡”。这说明临振县最晚在隋初就有设置,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设置的临振郡则是临振县的升级版,此后再无临振县。那么,县治故址还能找到吗?
清初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五《琼州府·崖州》载:“临川,州东南百三十。刘昫曰隋所置县也,属崖州。或曰本临振故县”。如此看来,临振县就是临川县的前身,临振县的核心区必在三亚河流域!县境达1500户,说明其范围有可能包含宁远河和藤桥河,甚至更宽广的区域。因为元代吉阳军为明清崖州前身,当时境内才1439户。大业年间升级为临振郡,郡治西迁宁远河,下设延德、宁远二县,仍旧以临振为郡名,符合设郡命名规则,譬如南宋的昌化军治就不在下辖的昌化县境。
汤沐邑,直观翻译为温水沐浴之地,实为抽取赋税的封地。大隋开国皇帝杨坚显然非常谨慎,将国之极南最偏远一个县域作为“汤沐邑”赐给异姓家族,从此将冼夫人与三亚大地紧密联系起来。冼夫人未必到过三亚,也未必到过海南,但是她与切实到过三亚的黄道婆的雕像一起,供奉在崖城学宫,这在历史上男权为主的中国社会极为罕见。有这么一个“汤沐邑”存在,绝对是冯冼家族的无上荣耀,激发了他们更浓厚的爱国情怀,历史上人才辈出,建树颇多。“汤沐邑”,亦为三亚河流域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大力挖掘其内涵,让冼夫人的爱国精神在这块土地上得到更好地传承。
临川县故址,在临春河畔“隐居”千年
时间来到唐朝,武德五年(622年)七月,冼夫人的孙子冯盎率部归顺大唐,朝廷在海南岛设崖、儋、振三州。振州即由临振郡发展而来,除了原有的宁远、延德二县,又增设临川、陵水二县。隋初临振县的余温还在,临川县又来了,它们具有延续关系。那么,临川县治到底在哪里?
光绪《崖州志》之《古迹》篇有两条记载。其一:“临川废县,在州东南一百一十里盐场西南山中”;其二:“临川场,在州东一百里临川村,洪武二十五年建”。有学者认定临川县治就位于临春社区,昔为临川村;但是这里属山谷短坡,极为狭迫,我在村中采访得知,早些年小孩上坡都得骑牛,还得手执棍棒防蛇和山猪,何况唐代,百姓建房速度还跟不上热带树木侵入的速度。文中的描述应指的是老临川村,这里曾是唐代的临川县和宋代的临川镇,由于三亚河网的变化,其行政级别逐渐降低。上述记载以崖城为坐标,临川村距州城100里,临川盐场距州城110里,相距10里。
临川盐场位于临春社区西侧,其西南自古为海域。“西南山中”,说的只能是今月川社区位置,小径往来相距约十里。相对临春社区,这本是西北方位,可看作古人的视觉误差。初到三亚时,我误以为三亚河是东西走向,实际上它是南北走向。这可能是因为三亚湾的整体弧度呈东西向,而州城位于西侧,加上临春岭也是南北走向,因此容易产生一种将西北方向误认为西南方向的错觉。
在此设县,背后的金鸡岭形如笔架,史志记载当时士子多往而拜之,祈祷学业有成,说明文脉颇深。唐初的金鸡岭还是濒海山岭,临春河在其南部冲积出一道堤坝,堤内为临川港,堤外为临川海。依山面海,坐北朝南,船舶直接靠港,有险可据,这正是冷兵器时代设置行政机构的绝佳位置。
直到民国,临春河仍旧称作临川水,可见该名字有着千余年的沿袭。宋代以前,琼南州县治署均无城墙,“只以木栅备寇”。在这里,金鸡岭昂首展翼,东南的山脉绵绵如屏,西南有浅滩出露,有效阻挡了巨浪,金鸡岭北有东西二河冲积初步形成的田园,临川县城更具有世外桃源景象,城址至今还处于“隐居”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临振水的名字逐渐演变为临川,最终在唐代初期设立了临川县。临川河不舍昼夜流淌了千余年,至今绿水汤汤,河流名称一直沿用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却误称为临春河,临川岭也“变成”了临春岭,名称的改变似乎割断了历史。若是附近修一条大道,建议就命名“临川大道”,一如本人提议并被采纳的“三亚里大道”,都是对三亚河流域古邑的一种纪念,让更多人了解三亚河的历史。
落屯县,自古都是三亚河流域的民族区域
《崖州志》之《沿革》篇载:“天宝元年(742年),改振州为延德郡,增置落屯县”。《古迹》篇载:“落屯废县,《元和志》永徽元年(650年)置,在落屯峒,因名。《舆地纪胜》即今黎中落屯村,在州东五十里……”
同一史志记载的落屯县设置年份矛盾,相差92年。《元和志》成书于唐宪宗年间,为李德裕父亲李吉甫著述,年代较近,可信度更高,大致可确定落屯县成立于唐高宗年间。当时的振州掌管五县,为琼南历史上设县最多的时代。落屯废县后演变成了“落屯峒”“黎中落屯村”,说明该区域自古以来都是黎族聚居区。
那么,落屯县治在哪里?
有学者将落屯峒归入乐东县内陆山区,但是这绝无可能!琼南地带,远离海岸线的山地即为游耕民聚居地,历史上与农耕民矛盾尖锐。譬如琼州的初设带有明确的防御性质,州治位于远离海岸之山区,在盛唐竟然陷落了124年。振州位于极南边地,落屯为其下辖小县,县治岂可远离海岸?当时海南岛上置县原则为陆路水路均须交通要冲,以河流入海口为佳。按照上述史志记载其实可以确定,落屯县的控辖范围为三亚河流域和宁远河流域之间那片密集的褶皱山地;距州城50里,正是担油港所在!担油港在唐代还要退后很多,同样是喇叭形,前方横亘着沙坝,形成天然港湾,如今担油港依旧保持这一形状。到了明代,这里还有一个落屯村的存在;因为河道短而窄,容易淤积,万历丙辰年(1616年)知州张宿主持疏浚河沟和港口,沟中还发现了一枚落屯县印。
此为天涯湾畔一块狭长平地,与北面多个山间盆地连通,州东驿道在此经过。陆海交汇,交通便利,得以建立县治。落屯县控辖范围东至下马岭、两王岭;西至南山岭、荔枝岭、象母岭;向北深入育才、雅亮、台楼、抱前、抱龙等黎族聚居区,至今仍旧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此置县,是大唐王朝绥抚政策的体现。这一带的大兵遗址发现了石器和古陶片,说明该地人类活动由来已久,却因为地形相对封闭,生产力发展缓慢,数千年前跟数百年前的陶器差别不会太大,大兵遗址也可能存留着落屯县时代的器具。
书志还有一种说法,《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的落屯县治为“崖州东北一百五十里”。按这距离,落屯县治也可能位于当时的榆林溪入海口,大致在今吉阳区下新村一带。当然,这只是纵览地理结合史志只言片语的假说,很多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推论。毕竟史书语焉不详,数据紊乱。当时统计的振州人口仅2821人,在大唐各州为倒数第二,设置五县更具有象征意义,县城建设肯定非常仓促,持续时间不长,变动亦频繁,且“只以木栅备寇”,很难存留遗迹。
无论落屯县治在担油港还是榆林溪入海口,均为三亚河流域,与临川县唇齿相依。二县处在同一个山环水抱的地理单元,位于三亚褶皱带,落屯县可算作大唐王朝在三亚河流域设置的第二个县。古往今来,在三亚河流域发生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留下过多少文化遗产?一切,还需要文史界更进一步地挖掘。
(三亚市人文地理学会会长 萧烟)






















